“谈起哲学时,姜汝旺意气风发、情绪饱满,眼睛里发出光芒,脸庞一时红润起来,不像是个耄耋老人。”5年前首次造访江山勤俭村的情景,单继刚至今历历在目。
此前,他曾见过形形色色的民间哲学爱好者,但大多数并不靠谱。有人神秘自称,已经预测到国家前途,要向中央汇报研究成果;有人画着奇怪符号,要去申请诺贝尔奖……
姜汝旺却明显与之不同,他的哲学思考冷峻犀利,饱经风霜的皱纹里,深陷着中国上世纪“全民学哲学”运动中的一段如烟往事,一如勤俭村村口那块“中国农民哲学村”的石碑,跌宕起伏,寂然暗淡。
“研究一个村庄的哲学史,可以见微知著。”被勤俭故事深深吸引的单继刚,开始组建团队,对这座走过兴衰荣辱的“哲学村”展开“解剖麻雀”式的深入研究。历经5年沉淀之后,研究专著《勤俭村遇上哲学》终于付梓出版。在单继刚看来,此书不仅是为勤俭村辉煌与落寞过往的“隔代修史”,更饱含着对那场特殊年代中涌现的众多学哲学用哲学典型的反思,期待读者“能够小中见大,在历史的镜鉴中思考当下和未来”。

在当地政府看来,勤俭村“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哲学文化,可以成为幸福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资源。
“这里早就被人遗忘了”

梦醒时分的姜汝旺再也不思功名富贵,他希望自己的家人都安心于做一介平民百姓。
1970年10月下旬的一天,邓颖超告诉正在北京出差的姜汝旺,你家里有灾难了,你赶快回去,参观的人太多了……
就在2个月前,当时的江山县勤俭大队(勤俭村前身),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转折的拐点,出现在8月16日。
当天的《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发了介绍勤俭农民学哲学经验的文章——《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并配发短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指出:“浙江省江山县勤俭大队,是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单位。他们的经验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特向广大读者推荐。”
置于文革年代,《人民日报》释放的政治信号迅速成为一道道政治号令。8月18日,浙江省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军民一定要反复地、认真地学习《人民日报》短评,学习勤俭大队学哲学的经验,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
这以后,前往勤俭大队参观取经,办学习班,开现场会的人络绎不绝,先是省内为主,很快扩散到外省。
江山资深媒体人士胡韶良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小山村热闹的景象:向来冷冷清清的勤俭,忽然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勤俭招待所、接待站,学哲学成果展览馆,在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的氛围中纷纷开张、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红脚梗”姜汝旺一举成了大红大紫的“农民哲学家”。新闻记者趋之若鹜,最多的一天,光给他拍照、摄像的记者就有29批……那光景,姜汝旺啥都不缺,唯独缺了“分身术”。
当地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文革结束前,勤俭大队在6年间大约接待了40万人次的参观者。浙赣铁路的毛家仓火车站,是离勤俭最近的车站,这个四等小站原本只能停少量慢车,但彼时却汽笛隆隆、蒸汽弥漫,常有快车临时停靠。
单继刚是在勤俭村农民学哲学陈列馆里,得知这些往事的。虽然已经时隔30多年,但透过那些清晰的黑白照片、泛黄的报纸书刊、斑驳的美术作品、亲历者的动情讲述,一切仿若就在昨天。
“当我还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时候,勤俭村已经成为全国学哲学用哲学的典型。当我后来成为一名哲学工作者的时候,这里早就被人遗忘了。”2011年10月17日,首次访问勤俭村之后,单继刚在感叹惋惜之余,萌发了念头,他想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对哲学村做持续的研究,“梳理其哲学事件,探讨其哲学特色,追踪其哲学进展,反思其哲学失误,谋划其哲学未来,力求为乡村哲学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力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一些鲜活的历史借鉴。”
此后,单继刚和同事马新晶、周广友三度造访勤俭村调研,他们访谈了大量当事人和知情者,搜集了大量文献素材,终于让勤俭村被风尘掩盖的哲学奇缘,重新清晰起来。
每次与勤俭村往日的“哲学明星”们对话时,单继刚总有一股莫名的感动:“桌子的这边坐着三个以哲学为谋生手段的人,那边坐着把哲学变为生活方式的人。这张桌子又把我们联系起来,就像哲学把我们联系起来一样。”
不愿再忆的伤疤

俭昔日风光无限的“哲学三姐妹”戴香妹、傅金妹、毛阿妹,竟一度对哲学失去了信心。
上世纪中叶,中国兴起了一场持续20多年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作为这场大潮中一朵耀眼的浪花,勤俭村的哲学辉煌发轫于文革时期,特殊的烙印使得这段往事如同流星般绚烂而短暂。
时代的逆转与落寞,令不少当事人不愿面对和提及这段往事。随着调研的深入,单继刚发现,勤俭昔日风光无限的“哲学三姐妹”戴香妹、傅金妹、毛阿妹,竟一度对哲学失去了信心。
曾任勤俭村党支部书记,连续当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戴香妹,在上世纪80年代卸任后,便把家里与学哲学活动有关的物品都处理了。
她家墙上原来挂着一张五届全国人大华东地区代表的合影,一次下雪的时候,融化的雪水从屋顶漏下来把它弄脏了,戴香妹对孩子们说,“不要挂了,妈妈不要了,过时了,人家看见也不好的……”最后,戴香妹索性将这张照片烧掉。
过去的30多年里,“三姐妹”经常见面聊天,谈话范围天南海北,东家长西家短,就是没有“哲学”。
“哲学”似乎已成为她们内心不愿再忆的苦痛伤疤。
当单继刚带着团队,决定揭开这些故事时,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的“三姐妹”不约而同地追问,“学哲学用哲学真的错了吗?”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与勤俭命运休戚相关的姜汝旺对此更是感同身受。
巅峰荣耀时,姜汝旺受邀进京,出入党政军各大单位,向中央的高级干部、北京的知识分子和外国政要讲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包括乔冠华、韩念龙、姬鹏飞、吴德、丁国钰、华国锋等人,都听过他的汇报。
在京期间,姜汝旺受到邓颖超、郭沫若接见,并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会面。
邓颖超在电视上观看了姜汝旺等人在北京电视台的报告录像,赞扬“姜汝旺同志讲得很自然,内容也精辟”,并表示“我们很受教育很高兴”。
郭沫若为姜汝旺题词:“一分为二对自己,赞扬声中找差距”“既当火车头,又当老黄牛”。
斯诺通过姜汝旺了解到浙江农村的一些情况。凯莱齐赞誉姜汝旺为“农民哲学家”。
1971年9月,取材于勤俭村哲学故事的越剧《半篮花生》在杭州演出时,身在西湖刘庄的毛泽东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此剧,并给予肯定的评价:“这个戏有戏,一家人都很可爱,说明农民不但可以学哲学,而且可以学好哲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革步入尾声,勤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文革落幕后,勤俭村更是盛极而衰,姜汝旺被列为清查对象,多次被抄家。
1979年12月,江山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姜汝旺案,以“反革命罪”判处姜汝旺有期徒刑5年。
虽然时隔3年,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姜汝旺案进行了复审,新的判决书“改判姜汝旺无罪”,但姜汝旺依然饱尝了身陷囹圄之痛,他的党员身份也莫名的消失了。
历经人生大起大落的姜汝旺告诉单继刚,自己足足看了5遍《红楼梦》才得以释然。他反复诵读贫病交攻的甄士隐偶遇跛足道人时,听到的那首《好了歌》,一遍遍地彻悟:“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昨夜的辉煌仿若一场春秋大梦,梦醒时分的姜汝旺再也不思功名富贵,他希望自己的家人都安心于做一介平民百姓,不问功成名就,只求一生平安。
“姜汝旺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深陷政治漩涡,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透过这段沉浮跌宕,也让单继刚对课题研究有了深刻的启迪:“审视勤俭村的哲学史时,必须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学哲学用哲学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把学哲学用哲学变成政治运动,从而使个人的命运服从于政治的命运,这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当单继刚和同事沉浸于探究勤俭村的哲学往事时,这个小村庄也在思索着哲学复兴的可能。
2009年,勤俭农民学哲学陈列馆开门纳客,其前身正是文革期间四方来客趋之若鹜的“勤俭农民学哲学成果展览馆”。
老树绽新花,传递的是勤俭村以历史为魂,发展乡村旅游的雄心壮志。早在2007年,勤俭村所在的江山市新塘边镇政府,便与江山市旅游局合作出台了一份“勤俭哲学村旅游区保护与开发策划书”,提出要重现勤俭“中国农民学哲学第一村”的历史风貌,为历史的追忆者和探寻者创造一片天地。
在当地政府看来,勤俭村“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的农民哲学文化,可以成为幸福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资源。
不过,勤俭哲学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昔日以“斗争哲学”闻名的勤俭哲学经验,对于当下到底还有多少借鉴意义?这一困惑,始终萦绕在当地政府的心头。
作为来自中国顶尖哲学殿堂的学者,单继刚的到来无疑给当地提供了专业级的智慧支持。
“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不管一个人是否意识到,他总是要接受某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指导,也就是哲学的指导。”单继刚告诉当地政府人士,工农兵学哲学运动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其正面意义还是超过了其局限性,当代哲学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不仅能够继续占一席之地,而且大有可为。
“勤俭村完全有可能以新的方式重现哲学的辉煌。”单继刚建议,不能把哲学封存在陈列馆中,要把它从没有生命的“展品”,活化变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做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阐释,同时更要让年轻人成为哲学传承主体。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新塘边镇党委政府,他们将新时期党员干部群众在日常工作中以哲学思想观点指导实践的事例编制成《哲学小故事新编》,以生动地保护好传承勤俭村的哲学文化历史。
很快,学了一辈子哲学的姜汝旺也有了新的用武之地。镇里请他出山主持“老娘舅工作室”,让他发挥哲学专长,化解乡村矛盾。
人生百味、人情千种,姜汝旺深知,改革开放后的乡土关系变得有些复杂和脆弱,宁静小村里,各种利益纷争每天上演,但世变理不变。
“大石头离开小石头砌不成墙。”他曾用当地谚语劝和一对夫妻,在外做生意的丈夫开始尊重妻子的想法和意见;“大可以变小,小可以变了。”他曾用这个道理让一对为土地征用费而争吵的叔侄冷静坐下来,最终商量出双方都满意的价格;“疑神疑鬼会害人”,他曾用这句俗话证明一户人家失火并非是邻居所为,让邻里恢复了信任。
“勤俭农民哲学的特色,在于大量使用本地独有的民谚、俗语、比喻、歇后语、打油诗,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提出了独特的哲学命题。”单继刚认为,恰是这种世代相传、久经考验的生活真理演变的哲理,赋予了勤俭哲学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它们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维系村民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
今天的勤俭村,随处可见模仿文革时期的墙画,毛泽东像章陈列馆也被列入新建计划。每天游走于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中,83岁的姜汝旺难免有些怀旧,他没有想到,曾经被一棍子打倒的勤俭哲学可以重装上阵;他更没有想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专家会为勤俭这个小山村著书传世。 “我们衷心希望,在中国的更多地方,能够盛开这种带有乡土气息、地域色彩、接地气的‘哲学之花’。它们一定美丽,而且一定能结出甘甜的果实。”事实上,单继刚已经在《勤俭村遇上哲学》一书的结尾,坦陈了自己和同事编写此书的初心:“哲学的大众化期待大众的参与。”(实习生祝镜涵对此文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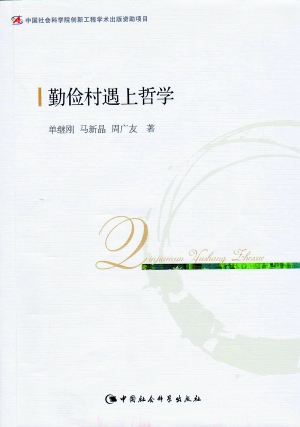
经5年沉淀之后,研究专著《勤俭村遇上哲学》终于付梓出版。单继刚认为,“研究一个村庄的哲学史,可以见微知著。”



 首页
首页 局馆介绍
局馆介绍 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 档案查询
档案查询 馆藏资源
馆藏资源 数字方志馆
数字方志馆 业务督导
业务督导 档案文化
档案文化 热点专题
热点专题 走进衢州
走进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