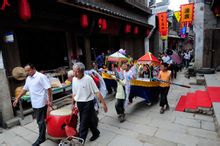名镇名村-江山市廿八都镇(三)
发布时间: 2014.03.12 来源:超级管理员
7、文物古迹
时代的印记
众多古建筑幸存了下来,当地人都说,从仙霞岭看下来,廿八都的古建筑群犹如一把弯弓,老街是弓把,205国道线是弓弦。
廿八都的兴盛主要是依仗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无论从江山、清湖,还是从福建浦城、江西广丰到这里差不多都是一天的路程,正好成为宿营地,当年之所以沿街有50多家饭店、旅肆,就是因此。
在数百年的繁华之中,廿八都并没有发育出近代的商业意识。哪怕在发财致富之后,商人们依然梦想着读书做官、科举仕进之路,文昌宫壁画的内容大半与此有关。他们在有了钱之后,首先想到的也只是建庙宇、修祠堂,最高的梦想无非是修文昌阁(宫)。值得深思的是,文昌宫竣工是1909年,大王庙也建于1909 年,其时科举早已废除,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早已风靡一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激起无数莘莘学子的共鸣。一年后,廿八都就出现了最早的一所新式小学。离辛亥革命枪响也只有两年了。
在小文昌阁,我们可以看到几百年前留下的对联:“读有用书行无愧事,说根由话做本色人”;在“德春堂”中药铺,我们还能看到百年前的“止咳保肺片”等商业广告;在街头里弄,在姜家旧宅,我们能看到人民公社到“文革”时期残存的打油诗、标语、语录以及漫画等。
从古到今,廿八都几乎完整地保留了每个时代的胎记。走进廿八都,最强烈的感受之一,就是这里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历史:一是黄巢开辟仙霞古道以来的 1100多年,廿八都作为一个三省交界处军事要地、商旅要道的历史,这有千年古道、史册记载及雄关险岭可证;二是数百年来作为重要商旅集散地从繁荣到衰落的历史,这有保存下来的老街、老民居及公共建筑为证;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及“文革”的历史,这有赛诗墙、漫画及大量标语、语录、对联为证,这样的地方即使在全国恐怕也不易找到了。
8商业经济
遥想廿八都的鼎盛时期,作坊栈行、饭馆旅店、商行店铺布满了整条弯曲的街道,日行肩夫,夜宿客商,布店、药店、煤油店、南货店、广货店……鳞次栉比。不过,即便是廿八都盛时也只有钱庄,有放高利贷的,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当铺。
商旅往来的频繁发展出了一种职业:挑夫,古道上每天都有上千根扁担在运货。挑夫一般都有组织,一来就是一队,有二三十人,几十担,一是安全(从仙霞岭到枫岭都有土匪),二是发货一般是批量的。江山船在清湖靠岸,大批货物长年累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翻越崇山峻岭,往来于浙江与福建、江西之间。
廿八都老建筑中最有特色的是楼阁式的木门罩,上覆黛瓦,檐角起翘,各个部件上又都有精致的木雕装饰。
问起1924年出生的金庆康老人,打他记事起廿八都最繁华的岁月是什么时候,他不假思索地说是民国16年到20年(1927k1931年),民国21年(1932)年以后明显就衰落下来了。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公路修通,从浙江到福建变得方便起来,廿八都的地理优势失去了。在仙霞岭的盘山公路开通之前,南来北往的货物主要靠的是肩挑,或者是独轮车(他记得小时候江西人还有独轮车队),廿八都是他们必经的歇脚地。
1933年11月,当作家郁达夫来到廿八都时,这里已经萧条、冷落。他此行本来是应杭江铁路局为杭州至江西玉山铁路通车之邀,顺道来探仙霞之险,看廿八都的古建筑,却正好见证了廿八都走向衰落的那一幕。
抗战期间,许多单位因躲避战乱迁到了大山重围中的廿八都,古老的小镇曾迎来短暂的热闹。抗战胜利后经济一派萧条,古镇一度重组商会,重建店面,试图重整旗鼓,但随着内战打响,时局动荡,商旅不通,加上公路、铁路通车后特殊地理优势的丧失,廿八都再也不可能恢复昔日的繁华,终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9民俗民风
在无数的谜当中,“廿八都”这个地名本身就教人琢磨。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须江建县时(931年即五代后唐长兴二年起,须江改名江山),这一带已有少量山民居住,地属须江县道成乡。
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江山县在乡以下设四十四都(“都”相当于村),从县境东北即现在的一都江开始,按顺时针方向以数字分别命名,这里排行二十八,故名“二十八都”(或称“廿八都”)。直到清康熙年间,江山县沿用明制,分十二乡四十四都,道成乡包括二十八都等四个都。这在《康熙江山县志》的地形图上可以看到。
不管经历多少王朝更迭、世变沧桑,无论在清以前叫都、叫里、叫庄,还是进入民国以来叫乡、叫镇,抑或是共和国成立后叫乡、叫人民公社、叫大队、管理区还是叫镇,“廿八都”这个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对于这个以数字命名的地名,多少年以后,日本华侨作家陈舜臣还在感叹:“像二十八都这样四个字的地名在中国是罕见的。”其实,这样的地名当初并不罕见,即使现在也不是仅有的,福建南平有一个廿八都,浙江嵊州市也有一个廿八都。在江山,类似四都、五都、廿七都这样的地名也都还在使用。
“官话”之谜
除了通行的“廿八都官话”,廿八都经常使用的方言至少还有9种,包括“江山腔”、“浦城腔”、“广丰腔”、“灰山腔”、“岭头腔”、“溪下腔”、“河源腔”、“下浦腔”、“洋田腔”等。一个方圆不过十数里的小山谷中竟然有这么多活的方言,确实算得上“方言王国”。据杨展三先生说,北京有一位研究语言的女博士,在杨家大院住了半个多月还舍不得离开,她说,中国的大部分乡村或集镇因为聚族而居,同村人往往同宗,姓氏、语言都比较单一,廿八都却是南腔北调,同时又有自己统一的方言——“廿八都官话”。
廿八都的民居建筑基本上是黑、白、灰三个色调,古朴淡雅。
方言的多样性最能反映廿八都移民的特征,“江山腔”、“浦城腔”、“广丰腔”无须多说,“灰山腔”实际上是江西宜黄口音。600多年前,江西抚州府宜黄县很多人到这里来开石灰窑,烧石灰,推动了廿八都造纸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并一直讲自己家乡的方言,他们的聚居地因此而叫做灰山,他们的方言被叫做“灰山腔”。灰山人卖了石灰,一定要买几两酒和豆腐坐在店里边吃边谈天,所以这里有豆腐店而兼酒店的,到民国时还有六七家,也算是一个特色。
“岭头腔”实际上是福建汀州方言。“溪下腔”是福建泉州、莆田一带方言,也称下府腔,是指福建下八府的方言。“洋田腔”、“河源腔”,是位于浙、闽交界的浮盖山麓两个小村落使用的方言,受浦城方言影响较大,又有所不同,基本上属于一种方言的变种。这些方言的存在大致上将廿八都先民的源头说清楚了。
最让人费解的还是“廿八都官话”,当地人也叫“正字”,通行于整个廿八都,和属于吴语系的江山话截然不同,形成了独特的“廿八都音系”(《衢州市志》)。不过它虽然保留了“官话”的特点,但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也受到了附近江山等地方言的影响。他们叫孩子为“娃仔”,女孩子为“女娃仔”。凡有小的意思都叫 “仔”,什么狗仔、猫仔、牛仔、猪仔、羊仔等,连小沙锅也叫“泥锅仔”或“风炉仔”。
这一语言是如何形成的?有一种说法是,清初在仙霞关和枫岭关之间设立“浙闽枫岭营”,游击衙门设在廿八都,“官话”就是驻扎廿八都的守关清军的通用语,“官话”其实不过是关外口音,因此也称“关话”,俗称“廿八都腔”。
廿八都人后来在遥远的东北丹东遇到知音,找到自己语系的源头不是偶然的。杨庆山老人说,抗美援朝时,镇上有几个青年参加了志愿军。部队在丹东停留时,他们吃惊地发现当地的方言几乎和“廿八都官话”一样,于是恍然大悟———“官话”不就是“关话”,山海关外的一种话吗?据说几位年轻人曾禁不住喜极而泣。
“廿八都官话”不仅远在东北找到了源头,而且近与衢州开化古代著名商埠华埠镇的方言,远到云、贵、川的语言都有神奇的相通之处,所以另有一种说法称,廿八都方言中云贵川语系占比例较大,因为当年与黄巢对阵的高骈部队多系云贵川人,也多有流落廿八都一带的。但这只是一种猜测,并不足信。
“百姓”镇之谜
廿八都(包括所属的13村)1万多人口中至少有146个姓氏,仅镇上的3600多人口中现在就有141个姓氏,是名副其实的“百姓”镇。据统计,现在的十二大姓是:陈、戴、王、李、谢、徐、刘、杨、黄、周、金、饶,昔日“四大家族”中的杨、金两姓还在其中,姜、曹已不是大姓,可见变化之大。
一般的乡镇都有百种以上的姓氏,但一村一地普遍都是聚族而居,某一姓氏占多数人口,而在廿八都146种姓氏中,人口数量最大的陈、戴、王、李四姓也不过是超过了500人而已,各占全镇人口的6.1%-7.5%,其他姓氏所占人口比例更低。
有研究表明,在这146种姓氏中只有40个姓是因婚嫁迁移原因造成的。由于地处相对闭塞的山区,人口婚嫁迁移的地域范围很小,这一因素对廿八都的姓氏分布影响较少。
造成“百姓”镇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的移民,虽然在146姓中只有47姓有历史迁徙地的记录,但这个47姓却占了总人口的近95%,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廿八都移民的来源,他们主要来自浙、闽、赣三省交界的江山、广丰、浦城,以及福建、江西其他地方(包括福建沿海、泉州等地)。从廿八都的方言来看,也是吻合的。
清初是一个移民的高峰,许多大姓都是这个时候迁徙来的。这些廿八都人的祖辈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栖息地,也并不是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多好,无非是他们原来的处境可能更加恶劣。廿八都四周的大山、关隘的拱卫似乎带来了某种安全感,尽管上千年来险峻的山岭从来没有使枫溪谷地免于刀兵和厮杀,但在一次次动荡的乱世中,相比之下,这块谷地还是要显得平静一些、安稳一些。特别是清代 “三藩之乱”后有过长达180多年的安宁,使得廿八都在商业上迅速繁华起来,移民纷至沓来,“百姓”镇大体上也是这个时候才最后形成的。
 首页
首页 局馆介绍
局馆介绍 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 档案查询
档案查询 馆藏资源
馆藏资源 数字方志馆
数字方志馆 业务督导
业务督导 档案文化
档案文化 热点专题
热点专题 走进衢州
走进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