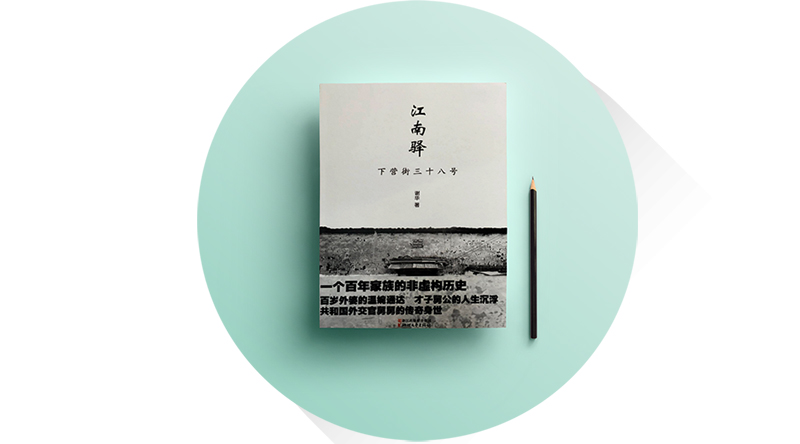
一、
外婆说,当年我们的太外公就是从这条水路上来的。
太外公携着家眷从绍兴逆流而上,到衢州码头后应该是登上高高的石级,再踏进水亭城门的。城门内沿城墙有条街,以水亭门为中心,一端往南,一端往北。往南的称上营街,往北的称下营街,上营街和下营街就这么隔着城墙与那条沿江的通广路并肩而行。
其实这上营、下营虽以“街”名之,其实并无“街”之实。据说这称谓是太平天国时屯兵驻扎时留下来的。虽然是不长的一条街,但上、下营也各有特色。上营富足,下营肃穆。下营街的巷口有周皇庙,巷尾有文昌阁,中间又巷中有巷,一条小天皇巷把它与天皇巷、天皇塔和天妃宫连在了一起。巷里也有一些大户人家,比如做丝绸生意的叶家的成片老屋、三房二厅的蔡家、小家碧玉的陆家……我们的周家老屋就在下营街的尾巴上。
二、
最值得一提的是老屋大门的门楣上那个砖砌图形。以前我们都没有在意,后来有人发现了,说是四旧,要铲除才好。可不知怎么又没有动手,只是在上面胡乱糊了一层石灰。时间一长,石灰脱落,这图形就一直保存了下来。我也好奇,细究,发现那是由三段线条构成的,中间一道为实,上下两道都中间断开,应该是八卦中的一个图像,朱熹称之为“离中虚,坎中满”的“坎”是也。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哲学概念,据古代的阴阳学说,坎主阴,如月,又是水木火金四象中的水。漫漫一百多年,屋变,人变,世变,事变,可这个“坎”字不变!
太外公缘何要为他这幢寄托了他后半辈子幸福的老屋打上这么一个印记呢?按说周家二代单传,应该旺阳气才对啊,徽州有个八卦村,叫呈坎,取的是以“坎”引水,以“呈”主阳,如此阴阳协调,天人合一。那太外公这个“坎”又隐喻什么呢?有个姓孟的朋友,在屋前屋后走了一圈,说“不要想得那么神妙了,从四周高高的封火墙看,老太爷很有防火意识,这个‘坎’大概只是想引水克火,如此而已。”
哦,真是如此而已也罢了,可如果老太爷能知道后来在老屋发生的一些事,还会这么做吗?
三
最后就是这棵墙角的腊梅树了,我曾经想,太外公栽下的为什么不是桂花、石榴、枇杷或是别的什么树呢。梅花主阴,本来阳气不足的宅邸,何苦再植一棵落完叶子才开花的腊梅?现在这似乎也有了解释,原来太外公也是腊月出生的,十二月二十七,那应是腊梅花开得最盛的时候。
不过,最让我感慨唏嘘的还是我的外婆也是生在腊月里的,而且是腊月初八。花刚含苞,娇媚无限,满院春色,指日可待。太外公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才选中了我外婆的呢?
据说,外婆嫁进周家,是太外公作的主。外婆的父亲是个裁缝,当时在兰溪的一个老板家做事,一个月十块大洋。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要往家寄八块大洋,这样他钟爱的小女儿(我的外婆华月英)才得以进了衢州淑德女子学堂读书。这是一个以教女红为主的小学堂,那个做了一辈子裁缝的老人原本也只想让自己心灵手巧的女儿学一点针线活计,却没想到小女儿品学皆优,毕业时争得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我听外婆说过这事,外婆说她本来是第一名的,后来被一个叫王彩莲的杭州人挤到了第二名。“什么叫挤啊,”我笑她,“那是人家比你好呢。”外婆不高兴了,说:“那是别人家里有来头。”呵呵,没想到这“一挤”竟让外婆记了大半个世纪呢!
可是世事难料,没想到被挤到第二名的外婆又却因此成就了一段在当时看来是攀了高枝的婚姻。据说那小学堂的王校长跟太外公认识,知道太外公在找媳妇,就向太外公隆重推荐了品貌皆佳的外婆。可耳闻总是虚,眼见才为实,太外公就叫了几个人一起躲在外婆必经的小天皇巷里偷看。那一天,毫不知情的外婆是梳一条油黑发亮的辫子,穿一身月白色竹布长衫,大大方方、漂漂亮亮地从几个藏藏掖掖的男人中间走过的,她不知道,这一走,就会走进一个再也走不出来的宿命之中。听说那天中午,太外公一回家就大叫上酒:“就是她了!”太外公一锤定音,太外婆就再也不提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了。亲事定在来年春暖花开之时。
四、
不日,太外公偶遇风寒。本来只是小疾,可不知怎么,慢慢地就成了大病,最后是卧床不起了。于是就急急地谋划,提前在年前迎娶,谓之材头亲,意在冲喜。
说也奇怪,新媳妇进门那天,太外公的精神真的好了起来,全家上下喜气洋洋,前厅后堂张灯结彩。到了下半天,天上有了太阳,太外公竟借一抹颤巍巍冬阳的支撑坐到了堂前的太师椅上。院子里腊梅开得正好,梅香阵阵袭人,可门口终不闻迎亲的鼓乐。
终于,太外公支撑不住了,就在太外公又回房躺下时,门外的鼓乐却热热闹闹地响了起来。漂亮的新媳妇终于进门了,太外公应该是听见了的,他长长舒出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醒来。
接下来,就是太外婆的天下了,她不动声色地关严了太外公的房门,堂前厅里,鼓乐喧天。迎新、拜堂,该做的都做,该有的都有,有板有眼,一直把儒雅的新郎,娇美的新娘,双双对对送入洞房。
就这样一直撑到子夜时分,一声凄厉的哭嚎,石破天惊,戳破了张着的灯,结着的彩。唰啦啦,红绸子换成了白绸子;昏惨惨,红灯笼变成了白灯笼。一眨眼间,喜堂成了祭堂,新郎成了孝子,整整一个月,新郎和新娘只能隔着太外公的棺木脉脉相望。外婆的人生之戏就这么在十七岁那年的悲喜交替中开场了。
那时的外婆肯定不会想到,82年后的她,也会这么苦苦地盼等着一场婚礼,新娘就是她钟爱的玄外孙女儿。礼物早就准备好了,出席婚礼的新衣服也做了,昏沉沉阴阳河间,庆喜的鼓乐还没有响起,盼媳心切的公公却已在黄泉路上迎她了……
悲喜之间,一个圆浑然天成。
外婆走了,走在她九十九岁的最后一个日子里——2001年的12月30日;我的女儿、她钟爱的玄外孙女嫁了,嫁在2002年的1月1日。
五
外婆说,每年腊梅花开的时节,外公就会做一首梅花诗送她。到了腊月初八,她的生日,帐幔上还会别一枝香梅。真不知那些月白风清的夜晚,梅香馥郁的帐内,会有多少卿卿我我的浓情蜜意留在这几纸梅花诗上!读林觉民的《与妻书》,每读到“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就会想起外婆外公那时的情景。归有光的《项脊轩记》中,也有“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之妙句,只稍把“桂影”换成了“疏影”就非常妥贴了。
院中的腊梅,就这样,成了外婆一生的图腾!
记得在外公八十岁阴寿时,外婆让我去外公坟上祭拜。自我上了中学,逢时过节,去鹿鸣山给太外婆和外公上坟就成了我的专职,一年又一年,这就成了例行公事,不光是我,就是外婆,也没有了上坟时应该有的悲悲切切。可那天我临走前,外婆却是欲言又止,最后,去屋里摸摸索索了好一阵子,才交给我一个纸包,再三叮嘱不能打开看,让我去外公的坟上烧掉。坟前,我抑制不了自己的好奇,还是悄悄打开了,原来是一套皂色衣裤,里面夹着一枝干枯的腊梅!
呵,十年的少年夫妻,五十三年的苦苦相思,在幽幽的火光中,扯成了一天缠缠绵绵的漫漫青云……
六
后来我在寻访杜瑰生老师时,又听说了一件事。他说外公是当时衢州有名的才子,不务正事,最擅长的是吹箫唱戏,戏是昆曲,还喜欢扮花旦。他印象最深的是民国16年(1927年)春夏之交,当时他上小学高年级,而我母亲刚上一年级,中山小学(当时在府山)召开恳亲大会,外公也去了。当时是林科堂任校长,他知道外公的才气,就要外公吹箫,外公就应承下来了。杜老师说,他还记得那曲子的第一句是“天淡云寒……”我惊讶他的记性,他笑了,说:“因为你的小姑婆(外公的小妹)的名字就是淡云呢!”可他当时才多大一点啊!我怀疑这应该是这位耄耋老人的幽默了。不过后来杜先生儿子在整理他父亲的一些随笔时,给我发来一则小诗,细细玩味,还真情深意切。
那个在恳亲会上一袭白衫、玉树临风般地优雅吹奏着箫管的真是我外公吗?是因为他对女儿的爱使然呢,还是因为他对音乐的爱才答应下来的?可不管是因为什么,这个叫洛仙的外公活起来了,在我的心中,在这个有些湿热的梅子黄时的午后。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五岁呀!率真、可爱;风流、倜傥,一个生活在梦中的年轻男人!
在无数个寂寞的日子里,外婆有时也会含含糊糊地哼几句小曲,里面好像有“人之一生,四季无常。春去渐夏,秋冬渐寒。草木黄落,九九归一……”的句子。“是外公教的?”我笑问,让她再唱清楚一些,她有点不好意思,就把曲子掐断了。
七
叶家遵守诺言,所以十岁以前,四姨对此事浑然不知。当时他们都在衢中附小读一年级,而且还分在一个班里。在四姨、舅舅七八岁上吧,有一年清明,他们各自被自己的养母带着去江对面的鹿鸣山上坟。事也凑巧,那天回来时他们坐上了同一条渡船。四姨说那天船上的人好像不多,两个母亲各自怀着心事,默然坐着,她和舅舅则在船上开心地嬉戏。四姨说这些时,我眼前就有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清明时分,江南草长,垂髫小儿,两小无猜。
不一会,船靠了岸,他们就又跟着自己的母亲各自东西。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四姨说,第二天到了学校,舅舅老是看着她偷偷地笑,四姨不高兴了,问他笑什么,舅舅说,你昨天脸上还擦胭脂,点眉心呢!说这些时,四姨倒也平静,只是觉得好笑,可细想起来,却让人感慨系之,当时小小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却在刚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结下了解脱不了的干系。



 首页
首页 局馆介绍
局馆介绍 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 档案查询
档案查询 馆藏资源
馆藏资源 数字方志馆
数字方志馆 业务督导
业务督导 档案文化
档案文化 热点专题
热点专题 走进衢州
走进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