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时间: 2014.03.10 来源:超级管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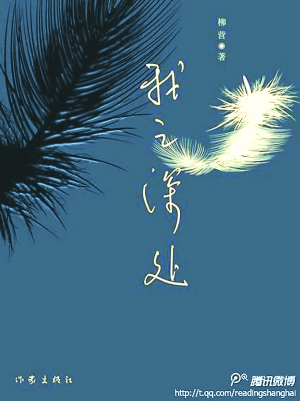

个人简历
柳营,浙江龙游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浙江省文学之星获得者,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入选者。在全国各大刊物《收获》、《十月》、《大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发表并出版的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阁楼》、《窗口的男人》、《蘑菇好滋味》,长篇小说《阿布》、《淡如肉色》、《我之深处》、《小天堂》等,作品被翻译至英国、法国、日本、瑞典等多国。
在70后女作家中,柳营是比较安静的一个。这种安静首先表现在她的文学行为方式上,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年代,柳营可以算得上单一。她只是在边缘处静静地阅读、思考和写作,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文学动作,除了以她的节奏发表作品外,她是不在意人们忘记她的。其次,这种安静还表现她对自己写作方式的坚持。她不折腾,自然而非刻意地与潮起潮落的文学大环境保持着距离。算起来,柳营的写作也已经十几年了,但如果从风格上说,今天的柳营与过去的柳营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她是在不断地前行,但她的进步是她自己的进步,如同一株杨柳,昨日的小苗已经长成大树,但她还是那棵柳树。而不像有些作家,今天那个系列,明天那种文体,如变脸术一样。我不是说后者不好,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柳营方式”,她是一种方式,她有她的意义。
对柳营与“柳营方式”熟悉的读者,是不会对柳营的新作感到惊讶的。他们已经被柳营塑造出了相对稳定的阅读期待。那里有南方气质的意象世界,水汽充沛,潮湿粘稠,山水交通,植物丰茂,穿行翻飞着许多倏尔即逝的小动物。那还是一个灵异的世界,充满先知、异兆与宿命,特别是暗夜中的故事,几乎与白日不相上下,不仅许多情节与细节发生在夜里,更有那么多的梦幻与魅影,它们的意义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相生相伴。但是,这种好像只能在前现代发生的叙述,却常常被柳营熟稔地植进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公司、白领、奢侈品、时尚与潮流性的都市消费方式,是她作品丰饶的土壤与杂色的背景,是在这种现代物质土壤消费气候中盛开着罂粟般的诡异之花。
当然,柳营的读者从没把她归入时尚写作和都市文学,因为柳营的作品大都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她的作品有着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苍老沉重的乡愁,而且,这种乡愁不只是一种情绪,一种诗意的修辞,也不只是永无舟楫的此岸对彼岸的眺望,而是人物内心的情结和宿命,甚至是人物一辈子都在进行的救赎。所以,在她的作品中,不管人物走得多远,成就多大的事业,他总要一次次返回他的故乡,那些隐匿在南方丘陵中的一个个小村庄,否则,他们无法说明自己,更无法解脱自身。
我曾经说过,柳营的写作是带有些自传意味的,这样讲不是说她都在为自己作传,自恋式地晾晒自己的生活,毋宁说她在为一代人写作,为一类人写作。柳营文学舞台上的主角永远是年轻人,他们与柳营的年龄相仿,大概的生活经历也相似。但要说到个体,命运就各有不同。概括地说,人生轨迹的大关节又有许多的重合面。他们出生在乡村,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不一般的童年,许多人物曾经在童年受到过刻骨铭心的伤害。他们或者通过求学,或者是流浪和出走来到城市。虽然许多人物从世俗的层面上看具备了相当的生存质量,甚至可以说功成名就,但内心的孤独与与生俱来的阴影,却迫使他们一次次改变生活方式,如轮回般地出逃、寻找、抛弃、重建,然后再打碎。如果用一个语词来言说柳营笔下的人物状态,那就是不停地流浪与自我否定,这种流浪与自我否定既是外在人生方式,更是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是柳营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是柳营对人生的看法,对世界的判断。
这样的阅读视野,是依靠柳营的长篇小说《树鬼》、《小天堂》、《淡如肉色》以及她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阁楼》、《蘑菇好滋味》等建立起来的,也同样可以说明她的长篇小说新作《我之深处》。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少年时的三个同学,雪竹、云雷和黑子。而小说的视点只在雪竹和云雷之间交替,因为黑子的生命被定格在13岁。雪竹是一个弃儿,在少年时期就受到养父的侵害,黑子一直生活在父亲的暴力之下,而云雷因为鬼使神差的青春萌动所引发的嫉妒,竟然放任黑子死在农夫私设的电网下……虽然各自所承受的伤害不一,但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和身心创伤。雪竹和云雷虽然后来都来到都市,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一直自处在灵魂的煎熬之中。都市的欲望、纷争和物质背后的空虚,常常让他们回首乡村,回首童年,回望少年时的欢乐、单纯和青春的萌动,但这样的回望又必然伴随着伤痛、追悔和对许多难解之谜的绝望,他们想回去,但又不可能回去,重返乡村只不过使他们的心灵雪上加霜。他们只能永远流浪,注定无家可归。
“柳营方式”从人物、题材与主题上之所以有种同质性与承续性,就因为柳营觉得他们这代人的故事还没讲完,更重要的是,他们灵魂深处的幽微还没有完全洞开,所以,柳营的写作呈现出纵向的特点,是一种不断向深处掘进的态势。而且,这种掘进不仅是对已然存在的勘探和开采,更是对可能性的想象与创造,因为对于柳营关注的这一特定群体而言,他们的人生还在继续,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在发酵,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心结随着外部世界的变更和人生遭际的演化,将幻化出新的镜像。
“柳营方式”不仅仅是人物与人性层面的,它还是文体与叙事层面的。熟悉这位70后女作家的读者都知道,除了中短篇,她几乎都在写作“小长篇”。柳营显然受到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比如“轻小说”,特别是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人物不多,线索单纯,多采用女性视角,回避宏大叙事,而且篇幅一般也不长。这种长篇体式,在有历史情结、现代小说是在欧美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影响下形成传统的中国,并不占主流。这一美学偏见现在到了纠正的时候了。因为一大批青年作家已经在这一长篇文体上做出了成绩,并且使这一文体趋于成熟和稳定。
我曾经认为,这是一种新长篇美学。这种新的长篇美学概括地说,首先是非史诗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远非前现代的行进方式,它们更理性、更日常、更细腻,也更人性化。其次,这种小说美学是下沉的,并且是趋向边缘的。如果说传统的长篇对政治、对社会的重大核心事件更感兴趣的话,那么新的长篇美学则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感性的经验,它不在中心,而在边缘,它在社会的神经末梢记录波动,在社会的微循环处收集样本。因此,这种美学必然是面向内心的,是向人的内心深处开发的。而从外观上看,这样的长篇是轻盈的,流丽的,精致的,它努力适应当代人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篇幅适中,具有可读性而又不成为负担,拿得起,又放得下。我说过,这样的小说美学,虽然同时面对来自传统巨型长篇历史化和来自类型小说欲望化的双重压力,但柳营却一直孜孜不倦,可见她对这一文体理解之深,自信之大。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这一件事,柳营做到了,她以她的方式做出了成绩。
(作者汪 政系文学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首页
首页 局馆介绍
局馆介绍 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 档案查询
档案查询 馆藏资源
馆藏资源 数字方志馆
数字方志馆 业务督导
业务督导 档案文化
档案文化 热点专题
热点专题 走进衢州
走进衢州